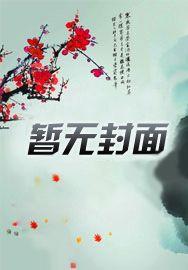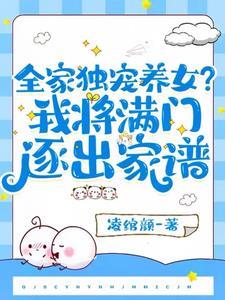山河小说>刑警追凶十年,终还冤死者清白 > 第225章 神探缉凶四十三(第1页)
第225章 神探缉凶四十三(第1页)
张局长对这种毫无组织纪律、肆意妄为的行为感到异常愤怒,他毫不留情地对某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自此事生后,市公安局内部再也没有人敢随意设假案来“考验”马玉林了。事实上,这种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。
在赤峰市公安局里,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收室的工作人员,从上到下,没有一个人再对马玉林那炉火纯青的追踪和鉴别技术存有丝毫怀疑。
马玉林凭借着自己对工作的兢兢业业、埋头苦干的精神,以及他那敦厚谦和的高尚品格,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。没过多久,他便被正式批准成为一名干部,并穿上了象征着荣誉与责任的警服。
与此同时,他的工资也得到了提升,达到了每月四十二元。
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学习到马玉林的精湛技术,局里特意为他配备了苗春青等三名学生,让他们跟随在马玉林身边一同工作,以便更好地传承和扬他的技艺。
此外,局里还特别将当时仅有的两头毛驴中的一头分配给马玉林使用,以方便他外出办案。后来,随着条件的改善,这头毛驴又被一辆自行车所取代。
在196o年,马玉林因其卓越的工作表现,被评为局里的先进工作者,这无疑是对他多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肯定和褒奖。
赤峰市平庄区队佛寺粮店,自开业以来,一直都是顺风顺水,生意异常火爆,每天都有大量的顾客前来购买粮食。
然而,就在这天早晨七点多钟,当这家店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回到办公室时,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——原本应该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六百多元现款和九千多斤粮票,竟然不翼而飞!
接到报案后,刑警队长史海滨立刻带领马玉林和其他侦察员火赶往现场。他们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现,犯罪分子是趁着店内无人的时机,从门上摘下一块玻璃,然后通过这个缺口进入办公室的。
进入办公室后,犯罪分子撬开了三屉桌的一个抽屉,将里面的现款和粮票全部盗走。
在进一步的调查中,马玉林在一块玻璃上现了一枚可疑的指纹。这一现让他兴奋不已,因为这很可能是破案的关键线索。
接着,他又仔细检查了地面上的足迹,最终在一个粮袋上现了板球鞋的印迹。凭借多年的经验,马玉林断定这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。
“怎么样?”史海滨急切地问道,“能追踪到犯罪分子吗?”马玉林深吸一口气,回答道:“试试看。”
此时正值七月,盛夏时节,青纱帐如一片绿色的海洋般涌起,将粮店周围环绕。这片高粱地宛如一片绿色的迷宫,茂密的高粱叶随风摇曳,出沙沙的声响。
狡猾的犯罪分子显然对这片地形非常熟悉,作案后并未选择走村道,而是像泥鳅一样迅钻进了高粱地,企图利用这片茂密的高粱林掩盖自己的行踪。
马玉林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,他的目光如鹰般锐利,紧紧锁定着犯罪分子留下的蛛丝马迹。
尽管天气炎热异常,高粱地里的绿叶层层叠叠,密不透风,暑气蒸腾,让人感到仿佛置身于蒸笼之中,但马玉林全然不顾,他索性脱掉了小褂,上身仅着一件背心,以便更好地在高粱地里穿行。
他一面用手不断地分开茂密的高粱叶子,一面全神贯注地搜寻着犯罪分子的足迹,脚步不停地追踪着。每一步都显得小心翼翼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史海滨等人在后面紧紧跟随,他们看着马玉林在高粱地里艰难前行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佩之情。
正走着,忽然,马玉林在一棵高粱边猛地停下了脚步,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高粱的根部,仿佛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他弯下身子,用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,然后似乎确认了什么,继续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。
史海滨见状,心中不禁有些纳闷儿,但他深知此时不能打扰马玉林,以免分散他的注意力,于是便将疑问压在了心底,继续默默地跟随着。
就这样,马玉林忽而钻入高粱地,忽而又走上村道,一路追踪,马不停蹄。不知不觉间,他们已经一气追踪了八里地。
时间悄然流逝,大约九点左右,他们终于来到了平庄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第三生产队。
马玉林继续追踪着,他的脚步坚定而稳健。沿途的道路崎岖不平,有些地段甚至没有现犯罪分子的足迹,但这并没有让马玉林犹豫或退缩。他心中充满了信心,坚信自己能够追踪到目标。
史海滨跟随着马玉林,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逐渐领悟到,虽然犯罪分子的足迹是马玉林追踪的主要依据,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条件。马玉林需要根据各种环境和现象进行分析,运用推理和判断,来确定追踪的方向。
马玉林追了一段路后,突然站住了。他抬头望向前方,目光落在了几间土房上。房前是一家的园子地,里面种满了各种蔬菜。其中有一块地种着豆角,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拎着小筐,在菜田里弯着腰摘豆角。
史海滨见状,也向马玉林靠拢过去。他们都穿着便服,看起来就像两个路过此地的行人。史海滨注意到,马玉林的目光不时地落在那个摘豆角的人身上,似乎对他产生了某种兴趣。
那个摘豆角的人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注视他,直起身子,好奇地向马玉林和史海滨这边张望着。过了一会儿,他好像摘完了豆角,提起小筐,向家里走去。
史海滨看着马玉林,疑惑地问道:“现什么了吗?”马玉林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朝着正在摘豆角的人走进的那座房子努了努嘴,轻声说道:“就是他。”
史海滨见状,心中不禁感到一阵诧异。他急忙将马玉林拉到一垛墙边,压低声音再次追问:“根据是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