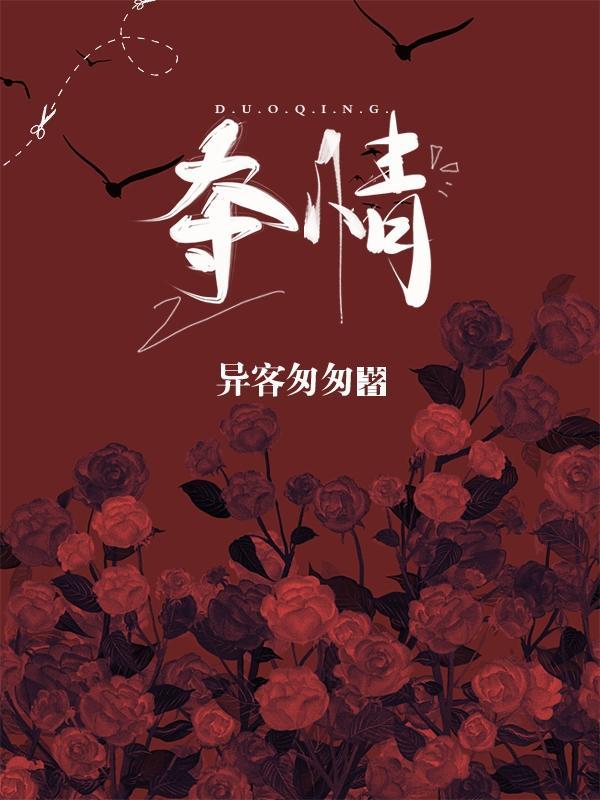山河小说>半路抢的夫君他不对劲 > 第507章 这叫拨乱反正(第2页)
第507章 这叫拨乱反正(第2页)
都是人精。
一路过来,随处可见本该解散的魏家军和忠勇侯名下多年未见的萧家兵。顺国公又是被那位逼死的,这……如何能怪他们多想?
迂腐的文官越走越快,脚步带风。已顾不得看路,布靴踩上地上一滩滩的鲜血,官袍下也跟着被溅上。
有人喊住贺诩然。
“那位便是罪恶滔天,可魏将军若牵涉其中,便有戕害君主之嫌。眼下时局动乱,帝王故去,只怕百姓愈发惶惶,涨外敌之气焰。”
“他虽喊你一声舅舅,可你别忘了,你是御史台的!”
“纵使圣上有万般不是,也轮不到他一个臣子正朝纲,礼崩乐坏啊!”
贺诩然不语。
他是御史台的不错,可又如何。
他还觉得魏昭做得好。
也有官员面色煞白,头重脚轻,生怕受牵连。
殿内。
应扶砚一夜未眠,身子显然有些撑不住,闭眼假寐,稍稍缓解不适。
“我……”
刚说了一个字。
萧怀言紧张:“怎么了?你要不先去内殿躺躺?”
应扶砚吐字:“我一想到要收拾狗皇帝死前留下的烂摊子就头疼。”
萧怀言:……
应扶砚:“需要好人替我分担。”
萧怀言沉默。
“怕什么,又没说让你。”
那你能叫动谁呀?
魏昭能理你?
突然,萧怀言想到了什么。
贺诩然啊!
那货精力可好!
每次审案可以好几日都不睡觉!
萧怀言松口气:“那你早说啊。”
“也不怪我多想,实在是你和魏昭那狗东西一样,都不太会做人。”
殿内已收拾过,尸体都扔去外头,也开窗通了风。
一时间无人再说话。
半晌,一旁顾傅居的嗓音传来:“来了。”
应扶砚缓缓睁眼,就见乌泱泱的臣子鱼贯而入。
迂腐臣子憋了一肚子的火。还没看清殿内有谁就高声。
“《春秋》大义,首重名分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天地纲常,卫将军却以暴易暴,以下犯上,此例一开后世乱臣贼子皆可效仿。”
“不遵礼法,长此往后人不将人,国不将国!”
“行了!”